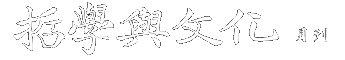編後語
邱建碩
輔仁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做為一個理性的人如何面對宗教與神學的問題,這是一個久遠但仍持續被關懷的問題。本專題以呂格爾思想為文本,從詮釋學的向度再一次地回應這個古老問題。黃筱慧教授在其〈論象徵的勾勒形構與宗教的向度——呂格爾詮釋學視野下的敘事之虹與敘事認同〉一文中,以敘事之虹說明了宗教與人之間的關係與其具有的張力。作者以為敘事者一方面可以透過宗教信仰中象徵的形構建立起這個關係,另一方面也在敘事認同的思想中,勾勒出自身的宗教面向。孫雲平教授的〈在宗教與神學裡的人——呂格爾的人觀〉以意志現象學、行動語義學和敘事詮釋學三個面向來說明人做為自然中的一個特殊存在,如何藉由行動來說明自身存在的特殊性,以及人如何與同屬性的存在互動並在互動中表明自身的存在。看在呂格爾眼中,宗教與神學是理解人不可或缺的元素,或者唯有在這樣的理解下,人才能是整全的。陸敬忠教授在〈從神聖語言出發:呂格爾詮釋學之生成發展脈絡之為神話循環或迂迴〉一文,嘗試從文本詮釋學、隱喻詮釋學和敘事詮釋學系統性地解釋呂格爾的詮釋學,並在體系性詮釋學的後設理論下思索呂格爾詮釋學對於宗教哲學之詮釋學轉向可能具有的啟發。沈清楷教授的〈呂格爾(Paul Ricoeur)正義與愛——一個未完成的辯證〉討論了呂格爾對於俗世正義與宗教愛的衝突的處理,惡的問題做為兩者的對話起點,倫理話語和宗教話語的背後雖有著不同的邏輯,前者是「平等邏輯」,後者是「超過邏輯」,但宗教的愛透過寬厚與世俗正義連接了起來。
如果要將語言當做理性面對宗教的重要關鍵,而理性與宗教之間又存在著一條難以跨越的鴻溝,那麼以下的問題就會隨之而生。首先,為何語言能夠做為銜接理性與宗教的橋樑呢?如果可以的話,什麼樣的銜接方式是可接受的?一個可能的建議是,無論宗教與倫理都有著談論「惡」的話語,它們的話語交集就是跨越兩者的可能性所在,這雖不表示這個交集就是連接兩者的橋樑,但至少也是一個找到這條橋樑的出發點。但什麼是這個話語交集呢?是基於它們有共同的對象嗎?若是的話,那麼找到一個共同的「惡」就成為一個必要條件。只是,這是否需要假定一個獨立於這兩種話語之外的「惡」存在呢?又或,這個交集中的話語使用著相同的語詞或相同意義的語詞,那麼話語所使用的語詞或它們的意義是否相同就成了需要得到關注的問題。但即使這兩種話語的語詞與意義都相同時,那它們所使用的邏輯是否相同呢?即這些話語連結的方式是否是相同的呢?例如,在某一種邏輯下,我們總是將同屬性的語言相連結,例如愛與愛的語言相連結,恨與恨的語言相連結。但在另一種邏輯下,我們可以將愛與愛的語言相連結,但不能將恨與恨的語言相連結,因為所有的語言總得與愛的語言相連結。只是,這兩種邏輯之間的關係又是什麼呢?它們之間是否又存在著什麼樣的鴻溝呢?當以每一個答案背後總有待解決問題的方式追問下去,這條鴻溝的跨越顯得那麼的困難與不可能。
那麼讓我們重新來看看這個出發點,即從「兩種話語的橋樑究竟何以能夠成為橋樑,並且什麼樣的方式建構這個橋樑才是可接受的」這樣的問題,轉向另外的問題,即這個橋樑究竟長的樣子是什麼?這是一種盡量地描述並展示談論「惡」的話語的方式,其目的在於將這個交集盡量的清晰化與擴大化。這是否能夠讓我們藉由填滿去跨越理性和宗教之間的鴻溝呢?事情並不會如此樂觀,當兩種話語存在著衝突時,除非排除了那些造成衝突的話語,而量的增加並無助於排除。但是,量的增加可以讓這兩種話語交錯的更加緊密、更加的不可分,即使鴻溝繼續存在,它們也仍是不可分的兩者。這會不會是一個處理理性與宗教的鴻溝的一種方式呢?
最後感謝本期的所有作者與審查者,作者們提出的精萃思想與審查者的專業建議共同造就了本期的成果。另外,還要感謝本期執行編輯黃玲鳳的細心與耐心,她即將在七月底離職,在《哲學與文化月刊》期間,為維護本刊的編輯品質所盡的一切努力,確實幫助本刊結出美好的果實,在此,僅代表本刊的所有同仁致上最誠摰的謝意,並祝一切順利。
Archive for 七月 12th, 2017
於 2017 - 七月 - 12
文章類別: 編後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