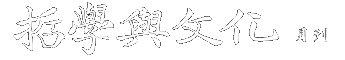編後語
黃信二
中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本月韓國儒學專題內容,探討十七世紀中葉以後,一百多年間韓國儒學重要的學術論辯,探討人之性與萬物之性同異的問題;此一題材是近年極少數分析「人物性同異論」的專題,不論是大陸或港臺三地皆少有學者研究,因此,本刊很榮幸能邀請韓國國立江原大學高在旭教授主編此專號,引介韓國學界最新研究成果,邀請全球關心此題發展的朋友,共享儒學於不同區域文明發展的情況。韓國儒學目前的發展模式,即如黃俊傑教授所提出:當代東亞儒學具有「脈絡性的轉換」(contextual turn)、「去脈絡化」(decontextualization)、「再脈絡化」(recontextualization)等的現象。他認為在東亞文化圈的人物、思想、信仰與文本在不同國家之間的密切交流活動中,最常見的現象之一就是所謂「脈絡性的轉換」:原生於甲地的諸多概念或文本,在傳播到乙地之際常被「去脈絡化」,並被賦予新義而「再脈絡化」;又於乙地的文化或經過「脈絡性的轉換」之後,傳入異域的人物、思想、信仰與文本,就會取得嶄新的含意,也會具有新的價值。因此,儒學在不同區域的發展,就會使研究工作觸及文本、思想或人物在文化交流的過程中,所出現的「去脈絡化」以及「再脈絡化」的現象。本期月刊所呈現出韓國儒學的內容,即是此種東亞儒學具有「脈絡性的轉換」的具體例證。
「人物性同異論」之爭議發展,主要起於1678年韓國學者因探討朱熹《告子章句》問題而開啟,此論爭影響層面廣大,包含韓國政治上的君臣關係、清代之中韓關係,亦包含民間主奴社會階級觀的變化,影響民間身份平等觀,故在韓國近現代的發展史上有其重有意義。本專題內容依下列次序安排:人物性同異論的「歷史發生、展開及意義」(高在旭)、「人物性同異論之成立基礎、栗谷哲學」(姜真碩)、「核心觀念的探討——理氣說、四端七情說、知覺說、未發說」(金哲運)、「主要人物——李柬與韓元震」(朴勝顯、林明熙)、「本爭論的後期發展與其意義」(李演都)、「專題書評」(姜真碩),從「人物性同異論」的歷史源頭至後期演變進行完整探討,其關懷焦點則從孟子與朱熹傳統的心性論的框架,逐漸轉換為人與物之價值差異的探討,依此而發展韓國儒學自身之獨特性。
在一般論著部分,本期刊出三篇論文:大陸浙江科技學院中文系張嵎教授〈孔門弟子對於孔子思想的發展〉一文,指出了孔門師生如何能形構一既有主導性特徵,但亦包含多元性發展的儒家學派。臺灣高雄師範大學經學研究所陳政揚教授〈從相偶論反思張載天地之性說的倫理向度〉一文,透過反思張載是否陷入「人有天地之性」的理論困境,分析尊朱或反朱子者探究「天地之性∕氣質之性」所引發的論爭。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朴素晶教授〈莊子音樂論之後世影響〉一文,則針對宋代陳暘《樂書》及朝鮮雅樂對莊子樂論進行討論。以上三篇文章皆有其創見與獨到之處,其豐富的內涵值得讀者細加品味。
本期的順利出刊除感謝高教授的主編與諸位學者賜稿外,更感謝臺灣與韓國兩地的審稿人嚴謹的提供審查與修改建議,同時亦感謝編輯部同仁的辛苦;值此爭秋奪暑之際,謹祝讀者能從中獲得豐沛精神食糧,並祝生活愉快!
‘編後語’ 分類彙整
於 2014 - 八月 - 31
文章類別: 編後語